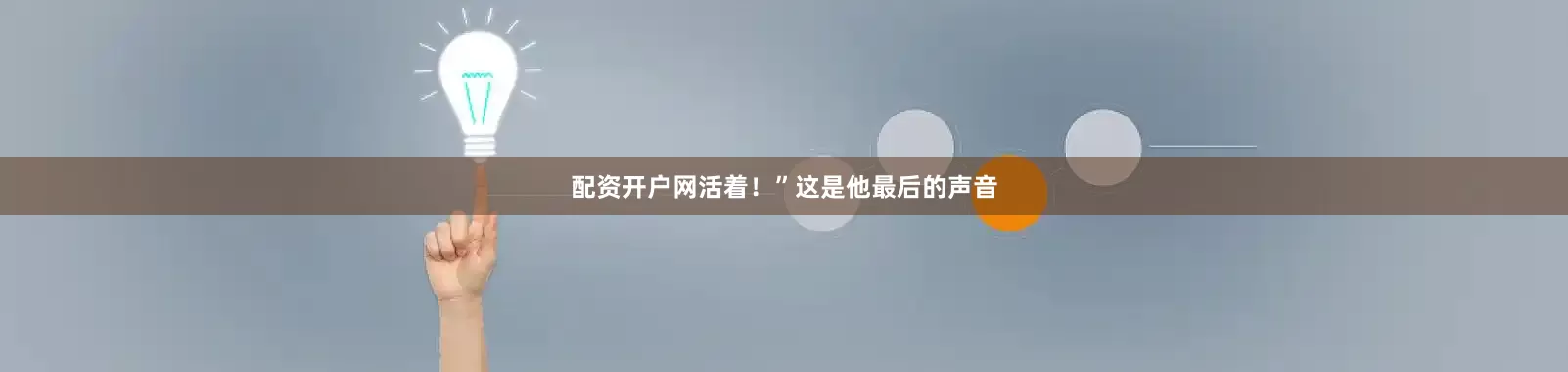
雪粒子砸在脸上,生疼。我缩在破败山庙的角落里,铁枪靠肩,上面挂着个葫芦。江湖上都喊我“断指老七”,名头唬人,可不管换了谁,在这风雪里熬上几个年头,都会觉得自己跟这山庙里漆皮剥落的泥胎,并无两样。二十年前,也是这般风雪,刀尖凝着冰花,比现在更冷。
还记得那年,雪深,能埋人。我和五哥循着“雪里青”那点血味儿,硬是从关外撵进了这老林。七天七夜,雪没停过。五哥脸冻得青紫,眼珠子里却恨浪翻涌:“老七,那杂碎就在前头!剥了他这张皮,给二哥祭旗!”二哥死得太惨,尸首抬回来时,连块囫囵肉都难寻。
雪里青是在处背风坡下被我和五哥发现的。当时他躲在个窝棚里,可只要凑近瞧,就会发现,其实只是几根歪斜圆木勉强搭出来个窝。我至今都记得那窝棚里的篝火,昏黄、微弱,可瞧在我和五哥眼里,却像野狼瞅见了羊。立时抽刀出鞘,猫了进去。
那时,雪里青正躺在块破毡毯上,面色灰败。可身旁却跪着个瘦小身影,正笨拙地替他擦拭着冷汗。是个娃娃,顶多七八岁,小脸皴了好几处,眼睛却亮得惊人,像寒夜里没被冻死的星子。
雪里青费力地睁开眼,看清是我们,嘴角竟扯出个笑,古怪,“小囡…药…药好了没?”
那女娃娃赶紧捧起个破瓦罐,药味弥漫开来,浓烈,刺鼻。五哥可不管这些,悄无声息刀尖已抵在雪里青咽喉,只需微微发力,便让他身死老林,“老七!二哥的血债就在眼前!”
展开剩余78%霎时,二哥那张总是带着笑意的脸猛地撞进脑海。他替我挡过致命一剑,我至今还记得,剑锋穿透他肩胛骨时,血点子溅了我满脸。“小七,活着!”这是他最后的声音,压在心口,比这漫天风雪更让人窒息。我喉咙开始发干,盯着雪里青那张脸,又看看那忘了哭的女娃——眼神清澈,像两枚烧炭,烫得人心慌。雪里青则咳着血沫子,眼神浑浊,竟有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平静。
“五哥,”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,“你看那孩子…”
“雪里青的种?正好!斩草除根!”他手腕骤翻,刀光如匹练,竟是那娃娃!
当啷——!
金铁交鸣刺耳,震得棚顶簌簌落雪。我横枪死死架住了五哥的刀。火星四溅,五哥眼中的惊愕与狂怒,瞬间爆裂。
“老七!你他娘的疯了?!”
“孩子无辜!”我咬着牙,枪杆上传来的巨力震得我虎口发麻,“江湖规矩,祸不及妻儿!”
“规矩?!”五哥的脸因愤怒而扭曲。
说实话,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。只知道,二哥若是活着,定然不会取那娃娃性命。可那时五哥眼里的冷光告诉我,这叫背叛,代价是此后无兄弟。
“规矩就是血债血偿!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,跟这杂......!总之今日连你一并了账!”五哥猛地抽刀,锐啸,不再有任何保留,狂风暴雨般朝我卷来。
窝棚狭小,里面挤着刀光枪影,碰撞、疯狂、绞杀。篝火明灭,映照着两张曾经生死与共,此刻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面孔。
雪里青蜷在角落,看着。那女娃缩在角落,小身板抖得像风中枯叶。
五哥武学颇杂,刀法狠辣,皆是多年江湖摸爬滚打练出来的路数。我太熟悉了,熟悉得闭着眼也能拆解。可越是熟悉,心口痛楚就越发清晰。一个错神的刹那,五哥手中刀直刺我心窝,我枪杆回援稍迟——剧痛从左手指尖瞬间炸开!不是被砍断,是枪杆格挡时,被刀柄硬生生砸碎了四根指骨!我闷哼,长枪几乎脱手。然而正是这一瞬的迟滞,五哥眼中凶光暴起,致命刀锋已如毒蛇吐信,直噬咽喉!
千钧一发之际,斜刺里一团黑影猛地撞向五哥!我和五哥虽然在交手,可眼风却一直扫着雪里青。可谁曾想经是那一直缩在角落里的女娃娃!她不知哪来的勇气,像被逼至绝境的小兽,用尽全身力气撞在五哥腰侧。他猝不及防,刀势大偏,贴着我的脖颈划过,带起一溜血线。女娃则被五哥护身气劲震得倒飞出去,撞在窝棚木柱上,软软滑落,没了声息。
我也首次在五哥脸上看到了丝茫然。雪里青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嘶吼,挣扎着想去够那女娃。这死寂伴着嘶吼,短暂,却比刚才的厮杀更令人窒息。五哥猛地抬头看我,眼神复杂,最终只淬成句冰渣子般的话:“老七,这笔账,没完!”
他撞开摇摇欲坠的窝棚门,一头扎进漫天风雪里,再没回头。
寒风卷着雪片灌进来,欲将篝火吹灭。我捂着血肉模糊的左手,看着地上昏迷的女娃以及角落里只剩一口气、眼神却死死黏在女娃身上的雪里青。
血债?情义?此刻都沉甸甸地压在这片风雪里,重啊。
后来才知晓,雪里青强撑着口气,抱着那女娃,硬是在风雪里爬了十几里,在一个猎户的窝棚边上,咽了气。女娃被救活了。有个常在关外行医的倔强医女收留了她。那医女,眉眼清亮,说话嘎嘣脆,像咬了口苹果。有次在林子里采药撞见我,叉着腰骂:“死脑筋!为了点子虚名,连金子活活蒙尘都不顾!面皮好看能当饭吃?”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。她骂得对。雪里青那张臭名昭著的面皮下,最后裹着的,竟是一点尚未凉透、属于人的温热。而五哥和我,这对曾以为情义坚过金铁的兄弟,倒成了彼此捅刀子的好手。
当然我估计大多数江湖人都会这么想,可自那次争斗后,五哥再没见过我。我有时候也会想,‘老七,这笔账,没完!’这句话到底作不作数。我有找过五哥,可他总是故意躲我,仿佛知道这次若是再动手,我肯定不会还手一般。
风雪依旧。我拄着枪,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到当年那处背风坡。窝棚的痕迹早被二十年的风雪和疯长的荒草吞得干干净净。只有两座矮矮的土包,一座埋着雪里青,另一座,是前年才添的——五哥最后一次与人交手,终究没能赢过宿命。
后来没过多久,江湖盛传,“七把刀”里的“恶五”面相凶戾,却有着断袖之癖,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个旧刀穗。那次我杀了很多人,我心里明白不应该迁怒他们,因为他们不知道,可我就是想杀,因为我没办法告诉他们,那旧刀穗是当年二哥教我编的,也是我送给五哥的结义礼。
我拧开葫芦,酒气在冷冽里弥散。一半浇在冻土上,渗入两座孤坟之间,一半灌进自己喉咙。雪还在下,盖住了旧坟新土,天地一片素白,干净得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血与火的腌臜。金子该发光?面皮会骗人?这道理,风雪知道,冻土知道,坟头那几茎枯草也知道,偏偏活蹦乱跳的人,总爱装糊涂。
我抹了把脸,不知是雪水还是别的什么。七个兄弟,如今独留我拖着副残躯,我不追究,也不想知道,因为只要往前走,总会听到雪落的声音。
发布于:江苏省a股杠杆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